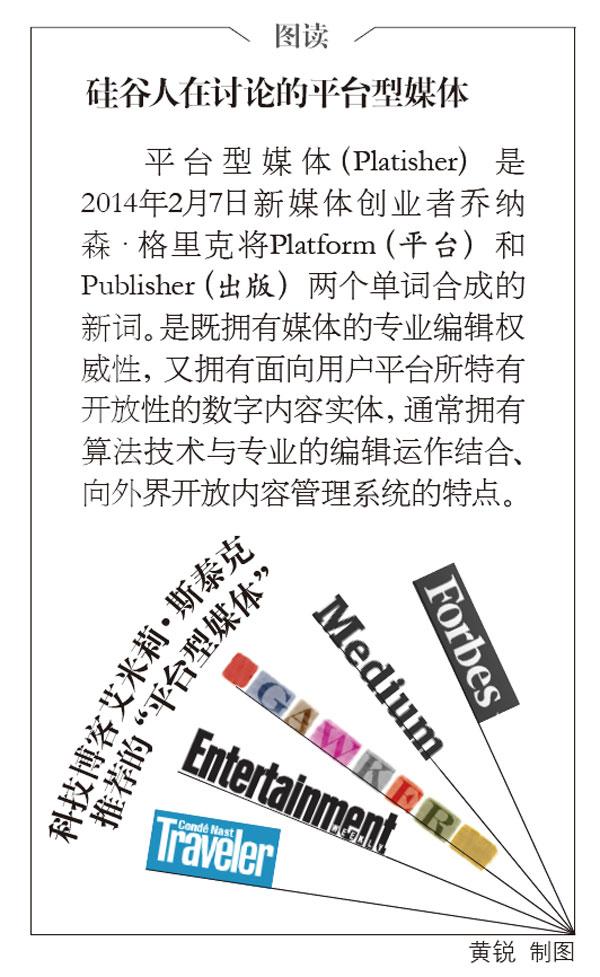
【回归内容】
纸张湮没“网事”中。现代报业诞生百余年来,传统媒体面临前所未有的技术革命。浪潮滚滚,传媒巨头萨默·雷石东提出的“内容为王”遭受着一轮又一轮的冲击。必须承认,基于承载平台的变化,受众的阅读习惯、媒体的生态环境、内容的生产机制、信息的流通渠道等,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于是乎,唱衰内容,奉渠道为神一时间成为寒冬论的主要腔调。
遗憾的是,经过几年野蛮生长,习惯借鸡生蛋的渠道商发现,这种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萨默·雷石东拍过一部经典电影《阿甘正传》,而“内容”,就像阿甘奔跑的双腿。2014年,回归内容渐成各方共识。11月,雷军招揽新闻门户教父级人物陈彤加盟小米,并宣布计划第一期投入10亿美元到内容产业,欲以内容串起生态链。自制剧成为当前网络视频行业一大竞争焦点,各大视频网站纷纷加大自制剧投入。如搜狐将2014年定义为自制剧元年,优酷土豆集团2014年在全面布局外购节目同时,更投入3亿元发展网络自制等。再看看现在风生水起的微信公众账号,成功的大咖都有高品质内容的创作和把控优势,网络上的信息繁多而重复,用户认可的内容才会主动分享和转发,这就是任何技术革命都无法击败的法则。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在不久的将来,对网民来说,或许不再有网剧和电视剧的区别,也或许不再有纸媒和网媒的区别,只有内容优劣,用户黏度。
时周特约记者 张自言
当记者有一些奇怪的习惯。例如需要写自己做自媒体故事的时候,我脑子里的第一个念头是:过程里的戏剧性不够,写出来没有可读性。
玩票的初心
为什么要开一个讲八卦的微信号。第一个原因是:身为一个纸媒从业者,很多想法是无法呈现在刊物上的。我曾经试图把这些内容尽量输送给供职媒体所在的新媒体,但很少能真正实现或是达到效果。第二个原因是:既然我在工作过程中想到的零零碎碎,聊天一定会说出来,不如直接记下来,万一有人喜欢呢。
我在网上做过很多件事,大部分时候应者寥寥,日子久了就放弃。在公众号开设之初,我对它的预期也是这样的,不过是给朋友们说几件好玩的事情,最多几百个人,试了几次累了就作罢。
这让我一开始甚至羞于在自己的朋友圈里转发我做的内容,让同事和同行知道我在做无谓的折腾,好像很不好意思。
奇妙的是,在我把第一篇文章发给朋友5分钟后,它就被转到了我的工作群里。
接下来就克服了那种不好意思,每写完一篇文章就自己先吆喝,我忘记了粉丝是怎样一天天地累积上去,也从来没有一觉醒来涨了好多粉的感觉。总之,关注人数每天都在一点点增加,第一次破万的时候我很开心,现在则经常贪心不足地觉得数字好像没变化—因为到五位数之后,万位上总不似千位、百位变化来得那么轻松。
有价值观的八卦
开始有媒体来问我运营经验,我常常纠正他们的问题导向:不,这里面没有经验、没有炒作、没有推广、没有盈利野心,什么都没有。我知道我看上去一定像个刻意强调自己心向艺术的八线艺人,虚伪极了。
但真的是这样。我的确没有刻意推广过。这恰恰是让我快乐的来源。我没有任何品牌和名望,但有这么多陌生人说“很好看”,这种认同和你在知名媒体上写一篇稿子是不一样的。
我是个悲观主义者,不敢寄望这个小爱好就能让我发家致富走上康庄大道。但我每天登录后台看到“再小的个体也有自己的品牌”那几个字时,还是会觉得很有动力。我认真做过很多篇报道,却不似这些杂七杂八的扯闲篇能让我迅速得到行业和大众的认同。我是一个奇怪的、对娱乐行业强调价值观的异类,只有在这个微信里,每个读者都告诉我:谢谢你给我们有智力的八卦。
最高兴的事情大概就是这样。我相信人们关心八卦是合理的,这是无法抑制的人性。但我也相信八卦是可以有格调的,你可以把女权和普世价值装在里面,当然一切都是有趣的。现在我证明了这件事。
什么是可传播性
这个小小的探索也改变了我对媒体的看法,传统媒体人认为的那种可传播的噱头,并不总是奏效的,甚至大部分时候是无用的。我第一次用八卦来议论韩寒和郭敬明的时候,做好了无人认同和掉粉的准备—我以为我是极少数—没有想到各种认识和不认识的人都在称赞我。
什么是可传播性?我现在反而想退回来说,坚持你的兴趣和你关注的事情。一件事,你每天都在和朋友们磨叨,那就是需要传播的东西。我发的内容,大部分是不会被通过、不好做、不能做的选题,但是它们可以在另一个土壤里生长得很好。
最大的困扰大概是时间不够用。编辑让我描述一下我是如何大病初愈还要坚持更新的。那时的念头其实是:“不把这点时间用起来,明天就更来不及了,我还要上班啊。”
尽管大部分阅读没有给我付费,我还是很庆幸无意中踩上了这个点。认同感可能是每个人的职业生涯里都想得到的,没有想到是业余爱好帮我完成了这个心愿。
我不太知道未来的样子。你不知道微信和公众号什么时候会被淘汰。但有两点大约可以宽慰:1.认真做内容总是硬本事;2.要尝试所有的新事物。
作者系微信公众号“严肃八卦”博主
另一面
持续颠覆时代的媒体融合
时代周报记者 吴筱羽
2014年末,各种资讯平台上都流传着《2014年,那些与我们告别的纸媒》这样感情复杂的文章。这一年,在新媒体洪流中投江的同行包括《竞报》、《新闻晚报》、《杂文报》、《心理月刊》、《今日风采》、《风尚周报》……
一年前的冬天,类似的清单也曾引发媒体人的恐慌,不同的是,那张清单上的“倒霉蛋”多是土豪时尚媒体,面临危机的原因也被认为是“反腐风暴”影响奢侈品广告大幅下滑所致。2014年的清单,则让人看到了真实的报纸业。
2014年美国市场共有190种新刊创刊,停刊的有99种,从数据上看相对积极。不过在过去3年里,北美市场新增刊物的速度已明显放缓。从2014年的数据来看,每增加2份杂志就有1份杂志停刊。当然,最糟糕的2009年没有重来—那一年,美国市场关闭了428种杂志。
传统媒体的转型是一个依然没有准确答案的世界性难题。否则,投资世界一流的计算机工程技术与设计机构、采取在线阅读收费、甚至在2014年10月裁掉了7.5%的采编人员替换成新媒体人员的《纽约时报》,也不会被认为放弃了转型。既然百多年的金字招牌都被认为将成为一块墓碑,那其他媒体的死亡似乎也没什么好让人折腕。
这一年,自动写稿机(WordSmith)代替初级记者写稿,代替记者“找到新闻线索”的软件也已诞生,技术进步的速度远远快于传统媒体们一边继续烧钱一边寻找转型出路的速度。这一年,中国传统媒体的媒体融合以大手笔投入为人艳羡,被《新周刊》评为年度新锐媒体的澎湃初期投资的公开数字为4亿元,同样生于上海的界面,公开的初期到账资金也有1亿元。然而,同时为人争议的是,众多吸引眼球的新锐新媒体,最大的创新依然是平台,内容生产以及运营收入仍主要是传统模式。
比新锐媒体们更具创新精神的年度关键词无疑是“自媒体”。2014年末,我们第一次看到各种“自媒体排行榜”,也看到以个人或个人及其团队为主体的自媒体,取代记者成为各种活动的嘉宾、广告投放清单上的对象。这一年,草根自媒体们废寝忘食地更新内容(当然,也有很多人废寝忘食地抄袭内容),终于成为比他们的前辈——博主更主流的媒体角色。从这个意义上看,微信越来越凸显的媒体属性,是中国式媒体融合里真正重要的一个推手。